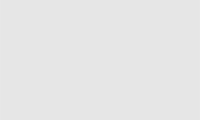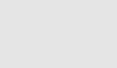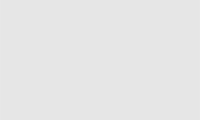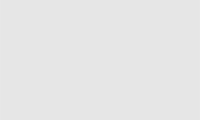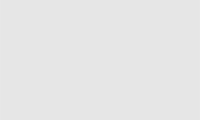口述实录:我曾想去做“小姐”的发廊妹
作者:吴迪
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小雪今年23岁,是河北承德人,来北京已经有三四年时间。“我16岁那年就不上学了,当时还想再玩两年,可我妈说先学手艺,于是就在老家学美发。学了大概两三个月,最基本的。”
-“刚一出来就被骗了,还是自己的亲戚”
小雪最初来北京闯荡的目的是开一个自己的美发店,她和一个亲戚带着从信用社借的几千块钱,打算投资,却被“杀熟”骗了一道。自己的店开不成了,她就转而应聘别的店的美发助理(小工)。想起第一次应聘大店时的经历,小雪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特有信心,人家问会洗头吗?我就说会,说实话在老家那边学的真不多,连什么是干洗都不知道。”店里的美发师傅让小雪给他洗头试手,评价是“手法挺漂亮,但是不怎么舒服”。“也许是师傅觉得我还挺可教的,就把我留下了。我学的挺快,一个星期就上牌了(从学徒转为小工),想想自己当时真是什么也不懂,挺傻的。”
-“我想过去夜总会当小姐,也想过要自杀”
小雪的家虽然离北京很近,但是经济状况却与普通的北京家庭有天壤之别。她来北京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帮家里还上外债。“在我的印象里,我家就没有不借外债的时候。我家现在还欠着五万块钱的外债。我爸去年因为脑溢血没了,他都病了三年了。脑溢血不能吃东西喝水,打一支高蛋白就要五六百元。我妈要照顾他,家里那四五亩地就跟我大伯他们家合种。我还有个弟弟,1986年的,不长进,没上高中,也不学手艺,成天只知道在外面混。家里人的生活全靠我一个人打工维持着。”小雪叹了口气,睁大眼睛很平静地说:“你知道吗?我曾经想过去夜总会当小姐。”“当小姐?你指的是那种工作?”“对,就是你们所说的‘三陪’。原来我觉得我爸没了可能会减轻我的负担,但是现在也没有,我妈又病了,弟弟整天在家呆着,不知道出来打工帮着补贴家里,反而老找我妈要钱。哪怕他每月挣100块钱也能减轻我不少负
担啊。我有一阵特郁闷,想过自杀,天天在河边溜达,总是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还上那五万块钱,靠我现在这么赚钱得还到什么时候?原来听说夜总会的服务员给客人倒倒酒什么的每月就能挣三四千块钱,挺轻松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那种事。可是要能把我家的钱还清了我也干,等帮我家把外债还清了,就跟他们断绝关系,让他们以后再也找不到我。”
老板的太太听说她要去夜总会,就一个劲地挽留:“妹妹,你要是干别的离开这儿我绝对不拦着你,咱可不能干这个,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毁了。”“我最终还是没走。因为自己又想了想,我不能为了挣钱毁了自己的一生。真要去了就完了。”
-“我不做那种‘保健’!”
小雪虽然想过去做“小姐”,但是真碰上这种事,她根本无法接受,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回老家,舅爷家的桑拿里来了两个要‘保健’的,我们那边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保健,那两个人说北京的小姐都会‘保健’。正好我在,亲戚问我会不会,我以为是真的保健,就说会啊,跟着到了店里。学美发的时候我是学过保健的,就是按摩一些穴位啊、足底啊,还是挺舒服的。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看见我就问有没有单间,我想这大白天的,做做按摩也没什么,他一进去就让我把帘拉上。我问他做保健干吗要拉帘啊?他马上就说‘你到底会不会‘保健’啊?我一看他那眼神才明白他到底需要什么服务,就觉得一阵阵恶心,当时就摔门出来了。”
“保健”那事以后有一阵小雪回老家的时候都不敢跟别人说自己在北京是做美容美发的,老怕别人误会是做那种服务的。后来她也想明白了,自己走的都是正道,又没做过那种事,没什么可怕的,所以人家问,就说是美容美发的,可是还要解释半天。“现在想想,解释什么啊,说了一大堆,也管不了别人是怎么想的,我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小雪长得很漂亮,也有客人约她出去玩,可她都拒绝了。前几天给一个广东老板洗头,要约她出去。“我听他那口气就说不去。他说‘你知道跟我们玩的那些人是什么人?是大学生,一个小时300元,陪我们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你看人家的钱挣得多容易。’我不干这种事!”小雪很惊讶,她很羡慕能上大学的人,自己也很喜欢读书,虽然一般都是借朋友的言情小说看。她没想到有的大学生出来做这种“工作”。
-“我可以当一个最好的美发助理”
可能大家觉得在美发店洗头也没什么特别,就是抹洗发水,然后躺在美发椅上给头发按摩几下。但是小雪说起给客人洗头的讲究来头头是道:“要舒服,就要泡沫多,又不能弄到客人身上。指甲不能留太长,也不能太短。”她伸出手,指甲短而整洁,“也不能完全没有指甲,有的客人头皮屑特别多,不留一点指甲挠不透,洗不干净。一开始我也觉得有些不习惯,后来洗得多了,也就好了。”
“我一共换过三个店,算少的。有的人说不换六七个店都学不出手艺来。我觉得自己这样挺好的。原来在东四那个店特别忙,从上午开门就呼呼地进人,最累的那会儿一天要站十二三个小时,没有闲着的时候,要给客人洗头,不能坐着。住在地下二层的集体宿舍里,我的两条腿全都肿了,连鞋都穿不进去,歇了好几个礼拜才好。当时我就发誓:再也不干这行了,说什么也不干了,太累了。后来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也是集体宿舍,大家住在一块儿。我一住地下室就起潮疙瘩,红的,一片一片的。可是后来又一想,为什么别人能住我就不能住啊?就搬了进去,现在也觉得还行。”
店里贴着“洗头免费按摩45分钟”的字样,小雪说按摩本来就是个最累的活,客人一多忙不过来。“洗完头要求按摩的客人多吗?”“多,10个里得有9个,剩下一个可能还是因为赶时间。就是帮客人按按头上、肩上的穴位,挺舒服的,可是我的手都酸了。一天下来可能都没知觉了。”店里的经理不用给客人洗头,挣钱多些,而且有能力就有可能从助理位置升职。小雪当过两个月经理,现在又下来了,老板说她还比较稚嫩,不够成熟。小雪倒也无所谓:“经理我做不来,太累。有朋友说要是换了别人从上边下来,肯定早不干了。一人一想法,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经理,但我可以当一个最好的美发助理,我要求自己做到回头客最多,干得最出色。”
-没有男友的小雪
小雪还没有男朋友,在老家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孩都有结婚的了,她的好友也都有了着落。她的妈妈着急,介绍了一个在北京开车运货的司机,也是承德人,离小雪家所在的村庄只隔一条河。“我们俩一般发短信。非典的时候特别郁闷,我跟他说‘提亲’,我妈当真了,天天催我回家,其实人家没那意思,后来这事也没有结果。现在觉得都不够了解对方,也就算了。”“想过找一个北京的吗?”“想过啊,可是北京男孩即使找外地女孩也不会找像我这样家庭条件差的。我老觉着像我这家庭条件的没人看得上。咳,这都是命,想也没用。”
“我都一个多星期没给家里打电话了,就因为提亲那事。其实我也心疼我妈,我知道她不容易。但是她太懦弱了,怕我弟弟,他一要钱就给。”小雪虽然染了头发,但是身上没戴什么饰物,只有一条很普通的项链,耳洞也是新扎的。她的妈妈最近也到了北京,现在在一家餐馆当保洁员,虽然挣得不多,也总算是减轻了一些负担。
-“我特感激我的朋友们”
小雪在北京的“家”离店不远,走路5分钟就到了。说是“家”,其实就是老板给店员租的集体宿舍。走进楼门,要下46级台阶才能到——一个位置相当于地下二层的屋子。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霉味,呆不了五分钟就浑身是汗。上个星期北京天气特别潮,“就跟睡在水洗的东西上似的。”小雪说。屋子里充斥着嗡嗡的响声,像是从管道里发出来的。宿舍不大,却挤了六张上下铺,还有三把店里淘汰下来的椅子。空着的床上堆满了东西,宿舍里还晾着不少衣服。她说,现在屋里住了七个人,其中包括老板的小姨和表妹。小雪的床上有一本反扣着的书,是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
屋里没有电话,要打只能去楼上的公用电话,或者去房东那里。洗漱间在宿舍旁边,地上全是水,根本没法下脚,只好架一块长条地砖当“桥”。里面有一个隔断,很破旧的木门,还上了锁,门上贴着张白纸,上面写着——“洗澡”。“是热水吗?”“是。”“那还不错,为什么上锁?”“收钱啊,洗一次澡五块钱呢。”小雪的表情有些无奈。
小雪每个月休息两天,不上班的时候,她一般都会去看朋友——一群同样从事美容美发业的年轻人,有时他们会一起去月坛滑滚轴,不过因为大家的休息时间不同,碰不到一块的时候小雪会选择在宿舍睡觉。就在半个月前的一天,夜里两点多,小雪突然肚子疼得不行,室友也都着了急,一个背着她走上那通向地面的46级台阶,另一个赶紧拨999、打车,忙乎了大半夜。小雪的口气有些激动:“我真的特感激我的这些朋友们,他(她)们都对我特别好。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回也是同一个男孩背着我,他的胳膊疼了好几天呢。”
-“我羡慕所有的北京人”
“有的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我给有些客人洗头的时候,他们一说话就是外地人怎么怎么着了,让人听着很不舒服。北京人都有种优越感,咳,说白了,还是自己自卑感太重。我们这个店经常有白领来,一做头发就花四五百块钱;还有跟我差不